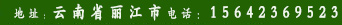|
原创江南三明治来自专辑纽约故事 文 江南 编辑 依蔓 3月15日的晚餐桌上,叮咚叮咚声突然此起彼伏地响起,手机上相继收到几条短信和邮件通知:由于COVID-19疫情严重,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将于次日开始关闭,孩子们的幼儿园随之关门,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系统也将同时关闭所有分馆。自此,大人在家工作、小孩晋级为失学神兽的日子正式开始。 “你们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了。” 两只小神兽欢呼雀跃。 “图书馆也都关门了。” “啊?!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呢?” 谁知道呢?通知邮件里的措词是untilfurthernotice,也就是说,君问归期未有期。 就在刚过去的那一周,我还按照工作安排,轮流在四家不同的图书馆分馆各待了几个小时。彼时已是山雨欲来,在离开每一处分馆时,我都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郑重道别,并往书包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绘本童书。这会儿一听到图书馆闭馆的消息,熊爸立刻跳起来,拉着熊哥熊妹跑到书架前,把我这周借回家的书堆在一起,来来回回数了三遍——共72本。我掐指一算,够读两周的。 全家大小四张脸上都露出了“我家有矿”式的诡秘笑容,和网上疯传的坐在卫生纸山上的人脸上的神情一模一样。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整整10周了。在这段所有人都足不出户的日子里,每天和无处安放的神兽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闪转腾挪着开无数个网络视频会议的我们,最想念的场所是哪里?最合口味的餐馆、最爱去的咖啡店、孩子们最喜欢的游乐场、科技馆、博物馆……于我们全家而言,答案就是图书馆。 尽管我把每晚的睡前读书从4本减到了两本,那72本书,也已经跟孩子们来来回回读过三遍了,家里不多的藏书也早就见底了。好在我家的神兽们还算容易满足,总有些书能让他们百读不厌。一本书读到最后,封底上常有整个系列所有书的封面照,那便是最引人畅想之处——“等病毒走了,我要去图书馆借这本,这本,还有这些,全部!”这样的话,神兽们每天都要重复几遍。显然,再百读不厌的书,也挡不住我们对图书馆里如列队士兵般排得满满的书架的思念,还有儿童区的玩具、拼图和涂色纸,故事会、手偶剧、周末的儿童观影会,轻轻松松就可以消磨掉大半天的日子,叫我如何不想它。 “我真想念我的图书馆。”一家分馆的馆长在邮件里这样写道。 我在回复中说,我,哦不,我们全家人,也非常想念它。 我对图书馆的热爱由来已久。当年初来美国时无所事事,整日流连于中世纪迷宫般的大学图书馆里,找一个靠窗的角落,或沐浴冬日暖阳,或对着一窗雨雪,窝在舒适的沙发里,偶尔学习,有时读书,总是发呆。那时,我的梦想职业就是大学图书馆东亚部的馆员。 那时候我们住在罗德岛,一到夏天总要开车去附近的海边沙滩或公园玩,每次去海边,都要经过一个名叫Warren的小镇,我们要穿过的那条窄窄的小街就是这个镇子的唯一一条街道,街边浓密的树荫下是一家家古老的小店,从街头到结尾也就不到一千米的距离。经过这条小街的人很难不注意到街边一座高高耸立的圆弧形墙面尖顶建筑,正面是青灰色的花岗岩外墙,宏伟而颇具历史感,在小镇的所有建筑中鹤立鸡群,十分醒目——我一直以为这座建筑要么是市政厅,要么是教堂。直到有一天,我因故要到这个镇的市政厅办点事,这才发现,市政厅在街道后面某处小巷子里,而街边那座最高大的城堡一般的建筑,竟然是一座图书馆,我走过大门口时,正见一队小学生由老师领着鱼贯而入。顿时,我对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心生艳羡,不为他们凭海临风的豪宅,不为他们院子里泊着的帆船汽艇,只为他们拥有一座占据全镇最好建筑的图书馆。 后来熊爸毕业找工作,我们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安娜堡。5年前初为人母,所有的风花雪月立刻离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儿歌、绘本、育儿经;我最常出没的地方,也从“阳春白雪”的大学图书馆转向了“下里巴人”的社区公共图书馆。 安娜堡的公共图书馆可以说是我作为新手妈妈成长的摇篮。医院的产前课上就看到图书馆的亲子活动介绍,熊哥出生后,我眼巴巴地等到他五个月能自己坐稳了,便迫不及待地带他去参加图书馆活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安娜堡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城,公共图书馆共有5个分馆,每个分馆的建筑各具特色,有的还是获奖的大师之作,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家分馆都有整面墙的落地玻璃窗,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使室内显得安静、宽敞、明亮又温暖;屋里的人也抬头可见窗外的风景,树林、草地、花园或者只是马路。 安娜堡图书馆采光很好, 孩子们在里面看书,阳光打在身上 从我家开车去这5座图书馆,最近的5分钟,最远的也不到20分钟。周一至周五,每天在不同的分馆有一场“宝宝时间”活动,我就每天带着熊哥去不同的分馆赶场。每场活动一个小时,由一位图书馆员主持,一位乐师弹吉他、尤克里里或其他乐器伴奏,家长们抱着宝宝在地毯上坐成一圈,跟着一起唱歌、读书、做律动、玩游戏,然后管理员抱出各种大大小小的玩具,任由大家自由玩耍。 还记得熊哥的第一次“宝宝时间”,遇到的儿童图书馆员是Ms.Sara,一位和那里的桌子一样圆乎乎的老太太,穿着颜色鲜艳到夸张的大花布裙子,灰白的卷发也弄得跟个鸟窝似的。一开场她就抓着两串铃铛,用小丑演员式的滑稽表情和声调,一边唱“Bellhorses,whatsthetimeofday?1o’clock,2oclock……”一边用自己的手臂模仿大钟的指针转呀转。最可爱的是她一手叉腰一手伸长,模仿茶壶的动作,唱Imalittleteapotshortandstout.Hereismyhandle,hereismyspout.配上她故意穿得更显圆鼓鼓的身材,实在是惟妙惟肖。至今,熊哥和熊妹只要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马上跳起来,一手叉腰一手伸长,歪歪倒倒地笑到歌都唱不出来。 有一天我还收到一封来自图书馆的邮件,标题是“Ms.Laura的告别故事会”。 Ms.Laura是一位满头银丝的儿童图书馆员,主持2岁以下的“宝宝时间”,也主讲2-4岁小朋友的故事会。她的风格是优雅自然型的,举手投足和一字一句间,流淌着一种无处不在的美感,我和熊哥是她的忠实听众。现在她要退休了,要办她的最后一场故事会。 那一天的故事会,不是在平时的活动室里进行,而是在进门的大厅里。平时空旷的大厅里这次挤满了人,其中有一大半是没带孩子的年轻人和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都是听Ms.Laura的故事长大的,这个小镇上的人恐怕有一半都是吧。活动最后,大人孩子都涌上前去,排队轮流与她合影。那一天,一位普通的图书馆员,俨然成了小镇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从那天起,我的梦想职业变成了,像Ms.Laura这样的儿童图书馆员。 图书馆发布的Laura故事会活动通知(供图:鸡蛋阿姨) Laura故事会的现场(供图:鸡蛋阿姨) 记得第一次走进安娜堡中心图书馆的少儿区时,我像触电一般被震撼到了,大概就是看到了“天堂的样子”那种感觉,到多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是清晰如昨。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少儿读物还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绘本、卡通、漫画、图文小说(graphicnovels)、非虚构以及各种专题系列。少儿区的藏书之丰富、巨量,让我叹为观止,对这里的小朋友们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羡慕嫉妒之情——那时候我还没当妈,所以只会将童年的自己代入情境。当然,现在回头再看就知道,那里的少儿区藏书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中远远算不上特别多的。 除了书架,大厅的另一半散落着矮墩墩圆乎乎的木头桌椅,桌上小筐里放着蜡笔、画纸和魔方、拓片、积木之类的小玩具。进门正对着借书台的桌上有个大鱼缸,色彩鲜艳的鱼在水草丛里安静地游来游去。门口有一张占据整面墙壁的世界地图电子屏,地图上四处散布着亮点,小朋友可以自己伸手去点亮某处,来标示自己的祖源地。大厅的另一端是落地玻璃窗,窗边用布沙发和低矮书架围出一个宽敞的角落,用作亲子活动的场地;玻璃窗上还有一扇门,门外是个小小的花园。 后来熊爸第一次到这里来,发出了和我当时一样的感慨:“我小时候家附近要是有这样的图书馆,我一定愿意天天住在里面。” 其实每次的“宝宝时间”,与其说是“宝宝时间”,倒不如说是“妈妈时间”。我在图书馆里学会了怎么跟宝宝玩,学会了如何给宝宝读书,学会了许多儿歌和律动游戏,学会了观察和引导宝宝的成长;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同龄宝宝的妈妈朋友,也为熊哥找到了他人生中最早的几位朋友。每次带熊哥来图书馆,活动散场后我们还会继续逗留,几位“妈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小家伙们则到处跌打滚爬,这里抠抠那里摸摸,看看鱼翻翻书,再凑在一起吃些小零食,轻松惬意地一晃就是半天。 熊哥两岁上幼儿园后,熊妹出生了,几个月后就接过哥哥的班,开始跟着我在图书馆里晃悠。那时的我,夜以继日地在小奶娃的吃喝拉睡中挣扎,沮丧、焦虑、困顿、疲惫、睡眠不足,每次在图书馆的时候,便是我将头伸出水面透一口气的最好时光。在那些“图书馆育儿”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那句著名的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Ittakesavillagetoraiseachild.)——小小的安娜堡正好被我们戏称为“安村”。 年夏天,因为熊爸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安娜堡,搬到了纽约。搬家之后,安娜堡最让我怀念的,除了夏天可以漂流戏水的休伦河,就是图书馆了。因为,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和安娜堡的很不一样。 安娜堡的图书馆大多时候是安静的,空间上也是宽裕有余。而到了寸土寸金的纽约,空旷安静就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皇后区图书馆有65家分馆,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停车场,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去步行可及的分馆。 于是我用推车推着熊妹、牵着熊哥步行15分钟走去离我家最近的图书馆,在查看活动时间表时发现,参加小朋友的故事会需要先报名登记。到服务台问管理员,才知道本月的故事会名额已满,只好等到月末去报名下个月的,更没想到月末开始报名那天,踩着图书馆开门时间赶到时,屋子里挤满了人,服务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我们还是没轮到下个月的名额,只能加入等候名单,得到下下个月的报名优先权……于是,在足足等待了两个月后,熊妹才第一次得以参加图书馆的故事会。 所幸熊妹也很快就上幼儿园了,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图书馆的拥挤和繁忙,毕竟这里是纽约。此后,我们转而只在每周末去图书馆,让兄妹俩玩玩拼图、涂涂画画,然后和他们一起挑一大兜书借回家。即便如此,图书馆依然是除了家和幼儿园以外,兄妹俩最熟悉的地方。 年是美国10年等一回的人口普查年,这次的人口普查第一次以网上填表为主要途径,在公共图书馆设有专用的电脑、安全无线网络等装备的人口普查站,供没有网络或设备的人们用以上网填表。一直想去图书馆工作,却因没有图书馆专业学历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我,找到了一个机会,成为一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口普查导航员,利用双语的优势,向人们宣讲人口普查,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提供帮助。我每周轮流在皇后区图书馆的4家分馆工作,法拉盛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 法拉盛图书馆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站在大厅入口处,看着川流不息进进出出的人,会让你觉得这里更像是个车站之类的地方。每天早上开门前,门口的台阶上就挤满了等着开门的人们。远远不止于借书读书,除了图书馆提供的各种信息咨询、培训和活动,还有很多其它机构和组织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这是一个集各种功能于一身的社区公共服务场所,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这里寻求帮助或解决问题。 第一次到法拉盛图书馆工作,馆长领着我在四层楼里上下参观了一圈,回到进门的大厅,扫视这里的各个角落,想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位”。进门左边是一列服务台和自动还书设备,正对面的一张长桌和整个右边则被纽约市民卡办理处占据。通道中央是问讯台,排成椭圆形的柜台圈出一片两平米左右的空间,工作人员就坐在里面。馆长最后决定将我安置在问讯台里。 那是3月初,疫情已经开始悄悄蔓延,往日门庭若市的法拉盛图书馆显得清静了不少,大厅里虽然依然座无虚席,门口进出的人流却和门外的主街(MainSt)街头的人流同时变得稀疏起来。馆长说,这几天人流量大约只有往常的一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尽管如此,坐在问讯台里的我,一分钟也没闲下来过。坐在我旁边的是“正牌”馆员John,花白头发,身材瘦小还略佝偻着背,工作起来倒是十分精神而且利索。他笑眯眯地一再跟我说,只要把上前问讯的顾客都指到他那边去就好。但他实在忙不过来,且有很多人是不会说英语,冲着我这张华人面孔来的;而我的本职工作,与人口普查相关的事,大多尚未正式展开。于是我顺水推舟地偷偷体验了一回我的梦想职业。 这天来问讯的顾客,有一大半是来申请免费代理报税服务的,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这里进行的服务,我只需指着楼梯的方向告诉他们去地下一层即可。 “请你帮帮我可以弗啦?” 我恍惚了一下,才勉强听明白这句纯正的上海话。 柜台外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太太,灰白的齐耳短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脑后,衣着洁净熨帖,脖子上还系着一条深绿底色的碎花小丝巾。 经过一番艰难的对话,我总算弄明白了她的意图:她想请我帮她报名,参加正在楼上开讲的公民考试培训,说希望能成为公民,因为她想要参加投票选举。 我于是搀着她坐电梯上到三楼,找到那个会议室,跟门口登记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帮她补上报名,并确认他们有中文服务,才送她进去坐下。老太太拉着我的手一叠声地说:“谢谢侬谢谢侬!”我看到有位华裔工作人员过来招呼她,这才放心离开。 才刚回到座位坐下,又听到一句带着焦急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抬头便见一张面色红黑的国字脸,眉头拧得像一张拉紧的弓——是个身板墩实的小伙子,身后还跟着个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两手紧拽着身前的背包带子,满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左顾右盼地打量着四周。 “现在这个病毒搞得严重起来了嘛,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免费医保的事。” 原来他们是想起前段时间听说过,纽约市会给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低收入居民提供免费医疗保险,他想咨询要怎么申请这种保险。 我转头问John,他说这里目前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建议他们上政府部门网站去查找信息。我转告后,小伙子说,“可是政府网站都是英文的,我看不懂啊,请你帮我查一下行吗?” 我低头登录进台上的电脑,花了五六分钟才找到一个有中文服务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屏幕转过去给他拍照。小伙子仔细地念了一遍电话号码,旁边的姑娘连忙拿出手机拍下,两人的神色都舒缓了一些,急匆匆地道谢离开。 后面有位大姐已经等了一会儿了,她走过来开口就问:“请问这儿卖书吗?”我说,现在没有,但只要办张卡就可以免费借书。 “我有卡,就怕借了忘记还,要罚钱的吧。” “可以在网上续借的,还书也很方便,在任意一家分馆,都不用进门,外面就有还书设备,塞进去就可以了。” 她迟疑着,又说,她儿子上高中了,除了上学就是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她很担心,想借些心理辅导的书回去给儿子看。我把青少年读物区的方位指给她看,并告诉她那边也有会说中文的馆员可以帮她,还是忍不住补了一句:“我建议您最好还是劝说孩子自己来借书还书,图书馆也有公用的电脑可以上网,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大姐满意地往青少年读物区走去。 这时,我看到之前那位上海老太又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姑娘,你人好,我还是再请你帮忙吧。” 原来她在楼上咨询了半天,自己得出结论——就算是有培训师帮忙,自己不会英文,入籍这事终究还是很难办成,于是她决定要学英语,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学。我暗暗咋舌,心想这样一位看上去至少得有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行动力和学习劲头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强,不知道她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楼下的成人学习中心就开设了不同级别的英语课,但不巧这天要下午一点才开门,我于是从密密麻麻的活动告示板上找出了英语课的单页,用笔勾出初级班的时间以及联系方式,交到老太太手里,目送她走出去。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整个上午我都在给这些人回答问题、寻求帮助,或者指引他们去找能回答他们问题的人——这就是John每天的工作。这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图书馆员工作的想象,也让我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开始工作前的多次培训中,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图书馆在本次人口普查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培训师给出的答案是,部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人口普查工作中的巨大障碍,解决方案是,与当地的各种公共机构、民间组织和社区团体合作,让人们信任的人去说服他们——图书馆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比如这里的John和我,就是人们信任的人。 那天在法拉盛图书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这种被信任、被依赖,也感受到了一种,暗藏在这个复杂多元的城市里,渗透到街头巷尾的,公民社会的文明的力量。 在我工作的其它三家分馆,我又见到了和法拉盛图书馆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这三家分馆都比较小,平时人也不多,比较安静。然而每到下午两三点钟,就会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因为这是公立学校放学的时间。 皇后区图书馆在二十多家分馆开设了免费的课后班,而即便是没有课后班的分馆,每到这个时间也会有很多中小学生涌进来,在这里读书学习,小组讨论,完成作业,当然也有吵吵闹闹和上网玩游戏的。在QueensboroHills图书馆,我看到孩子们坐校车过来,一进门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一边熟稔地和管理员拉闲话开玩笑,一边落座摆开作业书本。在少儿区图书馆员的座位后面,还骄傲地陈列着课后班孩子们送给她的手工作品。在离我家最近的Bayside图书馆,更多的则是老人从附近的学校把孩子接来,送进课后班,自己则坐在门口的沙发上读报纸看杂志。馆长Jean在忙碌中也会不时低声叫出某个中学生的名字,提醒他们不要吵闹,回头又跟我说,今天来课后班的孩子又少了几个,因为病毒的原因。 这时我才恍然明白,皇后区图书馆虽然从环境和用户体验来说远远不如安娜堡图书馆,但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如果从服务的人口数量和所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来看,其功能和效率其实可以说是更强大的。 在皇后区图书馆的人口普查台的工作照 就像对纽约这座城市一样,在搬来之前以及搬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不喜欢它,抱怨这里的脏乱差、拥挤喧闹和昂贵,想念安娜堡的宁静宜居;然而就在它成为疫情风暴的中心,很多人纷纷逃离之时,我却蓦然从“社交疏离”中的每一个社区、每一家营利或非营利的机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铺乃至每一个纽约客身上,看到了一种动人的力量,我突然与这座魔幻的城市发生了联接,对它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 3月16日图书馆关门后第一周,我们每天都在开会,头脑风暴,讨论我们可以各自在家里,做一些怎样的远程工作。第二周,在图书馆的网站上、Facebook主页上、Youtube频道上,就陆续出现了各种工作成果。首先当然是电子读物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儿童馆员们录制了读书讲故事的视频,其中还有西班牙语和英语、中英文双语的,每周定期在zoom上举办线上故事会,也有中文故事会,还有折纸手工课、少儿编程课。给成人的有线上的就业指导、瑜伽课、理财课、心理疏导课,也有移民法律咨询,新手妈妈互助组,有针对老年人的电话会谈项目,甚至还有名师的中国古典舞课。法拉盛图书馆的副馆长邱先生文学造诣颇深,便办起了线上中国文学读书沙龙。我们的人口普查宣传也不能缺席,我们在线上组织了西班牙语、中文、俄语、韩语、孟加拉语等多场非英语的人口普查答疑会,也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和研讨会。而最受欢迎的线上活动,则是一位嘻哈音乐DJ主持的音乐分享会。 在纽约疫情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闷在家里,看着飞速攀升的数字和骇人听闻的新闻,我常常会想起我在法拉盛图书馆遇到的那些人来,上海老太、年轻情侣、大姐和她的儿子,还有John,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好不好。 在皇后区图书馆的关门通报邮件中,还不起眼地提了一句:在不得不全部关上大门以后,所有的图书馆都保留了最后尚能保留的一项服务——免费无线网络。据IT部门统计,平均每天共有上千人次在使用各分馆的无线网络。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三三两两偷溜出家门的中学生,坐在图书馆门外临街的窗台上,低头专注地看着手机。我莫名地感到一丝安慰。 最近全美国都在筹划着各行各业的逐步重启,图书馆也不例外。自从我向家人透露了这个消息后,每次我开完工作会议开门出去,熊哥总会眼巴巴地追着我问:“哪家图书馆会开门?什么时候开?”我们都在盼望着,盼望着图书馆开门,盼望着走出隧道,拥抱光明。 原标题:《在纽约疫情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最想念的地方是图书馆 三明治》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luohun123.com/fcgs/13730.html |
在纽约疫情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最想念的地
发布时间:2023-2-17 11:13:39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建发岛内三盘案名亮相,产品面积段参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