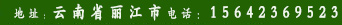|
拥有一个人或者一件物,一年还是十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更何况,谁都不可能完全属于谁。但凡你想霸占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而去。如果想通了这点,大概其他事情也不大可可能困扰自己太久。 这也并不是什么冥思顿悟,亦非什么看破红尘而四大皆空。就像今这天,阴冷又飘雨,年后的第一个上班的日子,似乎全世界都在抗拒着。 但,又只是冷,很冷很冷。 又一个年,在看似热热闹闹、举家欢乐、举国同庆下,幸福地度过了。可我也相信,这个年,绝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偶尔翻起朋友圈,都是大家小家、一帮人成群结队地出去游玩,那一张张脸庞,充溢着闲暇时分难有的美满。 有爱人、有孩子、有父母、有朋友,在衣食都无忧之下,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悦的? 我曾说过:不要擅自主张地去评定他人生活的悲喜,更不要用几个水墨文字、晦涩言语,就去概括别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纵使神灵,也无法决断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各种人情纷扰。 只是—— 只是,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置身于嘈杂拥挤的人群街道上,竟无一丝一毫的企盼。 新年,全世界都在欢度。攒动的人头、飞扬的唾沫、昏暗的白昼和一股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调料味,我忽然想起已故的爷爷,想起还健在的、住在老家的奶奶,想起十几年前,圆木与石块堆砌的旧房外,那一群浓妆艳抹、咿咿呀呀、哼哼哈哈的生旦净丑。那时的我,似乎什么都还不懂,趴在窗边,用力地吮吸几根指头的甜味,而我的大姐,还在用昨夜的剩饭,和着猪油煸炒。 我想: 这几年,或者今年,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是怎么庆祝的呢? 过年,没了年味。 虽然我也记不起什么才是年味,才是一个新年应该留给我的。只不过我很清楚,在朦胧的记忆里,如今的过年,并不是脑海中那个遥远的味道。 如果,不是鞭炮,还真不会去想起,哦,过年了! 玩游戏、烧烤、唱歌、看电影、聚餐,甚至去旅游……这些我们平常都在做的事情,哪一个,像在过一个年? 于是,有些人归罪于“手机电脑”,老人在埋怨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堕落”,更有人指出,大概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让过去的很多东西、很多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不再是只有过年才能得到了。 或许吧—— 又或者,人一旦不工作、不赚钱,就猛然间觉得无事可做,尤其是夜晚在家,何其的孤独和寂寞,难受得受不了。 旁边的父亲在和我的奶奶也就是他的母亲,大声地说着:“什么?一千?五百就够了!”一脸狰狞,极其的不情愿,又何苦为挣点薄面而纠缠着,这中国的人情世故,它深,太深,深到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的最里处。 忽而又想起昨晚接送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一路上,介绍对象,极力拔高我,然后又去暗暗地挑选着,他们互相比对着。而那一辈人们的见面,交谈的事情开始从“学习成绩”过渡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面子,攀比,总有可以拿出来互相炫耀的东西,就连“我生了儿子、他有三个女儿”都能说上好几年、好几十年。 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句话:“如果他带上孙子过来,我们见面金总得要吧!还好……”所谓的朋友,十几年的朋友,整个晚餐,我难以想象每个人的肚子里,是否都在盘算着什么?嘴里的阿谀奉承、冠冕堂皇,是否真心实意,那十几年的相识,那一瓶又一瓶代表着浓浓幸福的红白蓝各种颜色的酒,灌进心里,又是否真的心甘情愿? 而我,只是“呵呵”,在他们面前,我又回到小时候非常乖巧的模样。如今,我开始尽可能地去按照他们所期望的生活,也不再诉说着几乎没有人听得懂的句子,要不然,很可能,我要么是幼稚,要么成疯子。 我体谅母亲,她是个文盲;我同情父亲,他不过是一位历经了苦难、不愿自己孩子那样生活的历史潮流中的最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我无能为力,连对自己的父母,也无能为力。昨天,有人说,孩子长大,终于可以带着父母出去玩了。我也只是苦笑,附和,最后沉默。 这已经不是“不同世界、不同价值观”那么简单了,我,和他们隔着的是整个人生。 我翻到四年前写的一封信,很长很长的,是离开报社的时候写的。四年后的今天,我却仍然是那样一个人,不曾变过。 晶晶说自己不结婚,四年前也这样想过了,说我们比比谁坚持的久。 可是,我是会结婚生子,是想结婚生子。 我只是不想,他们让我结婚生子。 我想起雷雨里面的周冲,想起他的那一段话: 有时候,我就忘了现在,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夜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的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血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的世界。 是啊,我的世界,听说那里,草长花开。 过年了——不,都过完年了。 年2月22日 赞赏 长按刘云涛做客CCTV品牌影响力北京中科医院忽悠
|
我们是不是都忘了怎么过一个年了
发布时间:2018-5-19 19:48:46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帆船迷们注意了,3月可以到青岛看克利伯环
- 下一篇文章: 青岛一中帆船队第九次蝉联2017市长杯